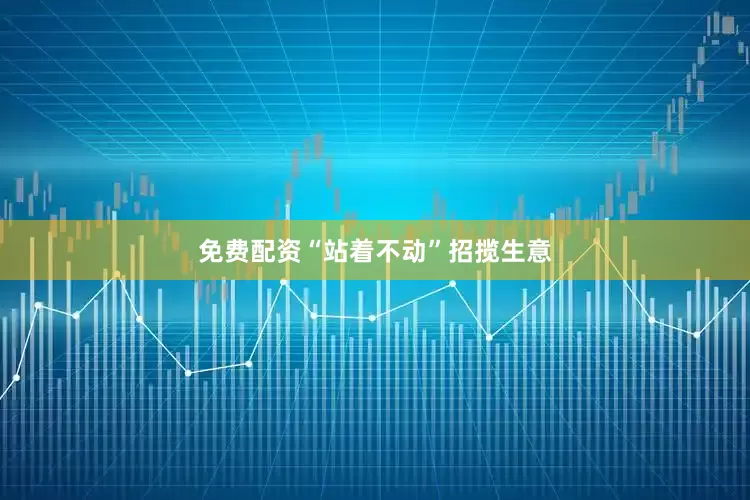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又站到了聚光灯下——但这次,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判决,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设置的“规则”,正反咬一口,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。事情的起点,是特朗普递交的一份请愿书,要求最高法院为他巩固任期内的关税政策“保驾护航”。
这本该是一次党派惯例操作:共和党大法官保共和党总统,这套路熟得不能再熟。可偏偏,他们曾经一手打造的“重大问题原则”(Major Questions Doctrine),如今成了最大的绊脚石。当初用它阻挠拜登,如今却卡在了特朗普头上——真是搬起石头,砸自己的脚。

敌我不分的“神兵利器”:从政治工具到制度陷阱
“重大问题原则”听起来貌似高深,其实说白了,就是大法官们给自己造的一把“否决总统行政命令”的剪刀。
这把剪刀的设计图,完全没有写进宪法,也没有国会背书,全靠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“拍脑袋”发明,理由很简单:凡是“影响大的政策”,就必须有国会明确授权,不能光靠行政机构自己说了算。
听起来像是为了防止政府滥权,实际上呢?从头到尾,这把剪刀只剪过民主党的布,尤其是拜登的布。比如2023年,拜登想给学生减免贷款,合法依据是《高等教育救助机会法》,这不是随便找的,而是国会白纸黑字写的。

可最高法院说:这个政策太重大了,国会授权不够明确,给驳回了。再往前翻,环保署想限制电厂排污,共和党大法官也用这招挡了回去。
问题是,这个“重大”到底怎么定义?经济影响?政策关注度?媒体热度?没人说得清。也就是说,这条原则有没有用,全靠大法官们“看心情”,今天说你重大你就重大,明天说不重大你就白忙活。
更离谱的是,这套逻辑从来没有用在共和党总统头上,哪怕政策影响再大,比如特朗普时期的减税、移民限制、环保松绑,都没人提“重大问题原则”。可现在,轮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——这下,剪刀对着自己人了。

特朗普的“超级关税”,到底重大不重大?
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是小打小闹,而是一场涉及全球、覆盖数万亿美元的贸易大改造。他自己都说,这是“美国经济与外交的核心武器”。
2018年起,他对中国、欧洲、加拿大、墨西哥等国商品加征关税,并动用《1962年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,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,赋予自己几乎无限的关税制定权。
根据耶鲁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,这一政策让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约2400美元,十年下来相当于变相增税2.7万亿美元。这规模,别说学生贷款减免了,连整个教育部的年度预算都不够比。按“重大问题原则”的标准来看,这不重大,什么才重大?
可问题来了:如果大法官们真按自己设的标准来,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就该被一票否决。但他们会这么做吗?恐怕没那么容易。

共和党大法官们已经开始找“下梯子”的路了。布雷特·卡瓦诺大法官曾提出“外交政策例外论”,意思是:只要打着外交旗号,就不算重大问题。还有人说,这次是总统自己亲自下令,不是哪个联邦机构自作主张,所以“重大问题原则”不适用。
这套说辞听起来很巧妙,其实是把法律当橡皮泥捏。问题是,之前的判例从没说总统亲自下令就能跳过国会授权。而且,外交政策就能随便搞?你用外交名义涨税,我也能用同样理由搞医保,那法律还有啥边界?这不是解释规则,而是拿规则当挡箭牌,只对敌人用,自己人豁免。
托马斯大法官在一个附议意见中自己都承认,这个原则“缺乏可操作的法理标准”。换句话说,根本没个谱,全靠主观判断。用这种“空中楼阁”的规则来裁定现实中的重大政策,不仅扭曲法律,还把法院自己也套进死局。

自作聪明的代价:最高法院的信誉正被蚕食
现在,最高法院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题:要么继续坚持“重大问题原则”,那就得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打回来;要么给特朗普开绿灯,那就等于公开承认,这个原则根本是双标工具,只用来卡民主党。
这就是典型的“卡尔文球”逻辑——我定的规则,别人必须守,我自己可以随时改。但法律不是游戏,更不是私家花园。最高法院一旦表现出这种选择性执法的姿态,它的权威就不再基于法律,而是基于党派。
据盖洛普2023年民调,美国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经跌到47%,创历史新低。而且,学界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。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保罗·克鲁格曼指出,最高法院“正越来越像一个政治机构,而非宪法守护者”。

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历史节点。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,共和党大法官强行终止佛州重新计票,直接决定选举结果,引发巨大争议。现在,如果他们再次为党派利益牺牲司法一致性,那等于是在历史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。
更大的问题是制度性后果:今后任何总统推动行政措施时,是否会先考虑“这会不会被最高法院用‘重大问题’卡死”?而不是“这是不是对国家有利”?当法律变成政治工具,政策的起点就不再是人民利益,而是司法风向。

被自己套牢的“卡尔文球”:从政治得分到制度反噬
共和党大法官当初打造“重大问题原则”,原本是为了制衡民主党总统,结果现在却成了限制自己党派的“回旋镖”。这不是简单的打脸,而是制度设计的自我反噬。
从短期看,他们也许可以再想办法“豁免”特朗普,保住党派信誉。但长远来看,这种“只对敌人有效”的规则,迟早会让整个司法体系失去公信力。当法官不再被看作中立裁判,而是党派代理人,那法院就不再是“最后的防线”,而是政治斗争的舞台。
民主党已经开始推动最高法院改革,包括增加法官人数、设定任期、限制司法权扩张等提案。虽然短期内难以落地,但这场关于司法独立的争论,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讽刺的是,那条曾经被共和党大法官视为“神兵利器”的重大问题原则,现在却成了他们无法卸下的枷锁。这说明,法律一旦被过度政治化,最后受伤的不只是对手,而是整个制度本身。
最高法院不是棋盘,法官也不是政客的棋子。当规则只为一党量身打造,终有一天会卡住自己人的喉咙。特朗普的请愿案,不只是一个政策争议,更是一面镜子,照出了美国司法的深层困局:当信任流失,制度就开始松动;当法律沦为工具,民主就开始失声。
中国股票配资网上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怎么配杠杆很可能就会沦为双方争斗的牺牲品
- 下一篇:没有了